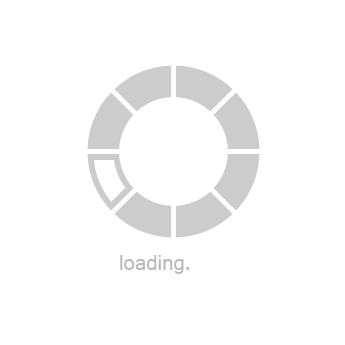如果说每个季节都有对应的音乐,那春天一定是后朋克。出门踏青,你会看到林间的小路上,树、花、草这样的被子植物在欣喜地抽蕊吐叶,在枝条的尖端冒出嫩绿色的头来,就连道路上原本泛黄的苔藓、小水洼中慵懒漂浮的水藻,也悄悄地加了一层浅绿的薄毯。这是吉他扫弦的清新。然而,春天的云却是不讲情面的。它们阴沉在天空上,簇拥着挡住了太阳,只余下淡淡白光,堵得天地万物都阴沉且泛白起来。这种色调,宛如贝斯律动的低沉,还使电吉他的音也失真,浪漫、荒诞。春雨在云的掩护下奔向大地,却一头撞碎在上面,散落晶莹的涟漪,沙沙地散发南方特有的潮湿味道。时不时远方劈开闪电伴随清脆雷声,是虫子们暴躁的起床铃。这些,无疑是隐藏在音乐中的鼓点了。
但仿佛还缺了些什么。
对了,是人声。清明扫墓,是春天的一大民俗了。家家户户约定俗成的,纷纷聚在一起,大大小小,有的面带喜色,像踏青郊游;有的凝重,这是对祖祖辈辈的敬重;眼圈红肿,面露悲哀的,定是刚离了至亲之人,心里的痛楚如石头般沉甸甸压着的。有的人想着死,有的人思着活。但有一类人截然不同,他们挎着篮子,低着头东找找,西看看的:那并不是丢了什么东西,而是在进行时令的劳作——采绵菜呢。那一株株长着如汗毛般洁白而柔软的野菜,叶片也软软的,扁平的一小窄条,尖端是略胖的半圆形,有时还开着如同一团小米粒似的金黄的小花。这便是绵菜了。他们弯腰仔细地看,采摘那些小株的。那些醒目的开了花的,他们并不采——太老了,口感太韧哩。只有小孩才把这埋汰货宝贝一样搂一大把,兴奋地跑来跑去炫耀他采得多呢。
采完了,后面的工序便与小孩无关,是大人们执行的步骤了。我自然也是不甚了解,毕竟作为一个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嘛,吃现成的就好了。不过根据成品来看,仿佛是先把绵菜煮烂了,再将其和糯米面团夯在一起,里面添上咸菜、肉末、豆腐干条一类的馅,蒸熟,就算完成了。好的清明团子,有拳头般大小,表面光滑,还能看到皮上浓淡不一的绿,是绵菜的存在。抓起咬一口,你就能发现这皮是薄且极粘的,还留存着绵菜的柔软;馅最好淡而有味,不盖住绵菜清香的同时又增添鲜美。独属于温州清明的味道啊!
但这清明团子最特色的还是它的内涵。清明啊,是一片同时笼罩着活人和死者的浓雾。后朋克,则像人在将死之时,躺在一张残破的沙发上,微笑着透过窗望夕阳下炮火纷飞。它对于人而言,是代表死的,谜一样的,残酷的,但同时也是美的。它仿佛在低声呢喃着:“你之前会有人死的,你之后是有人死的,你终究也是会死的。所有生命都将逝去,就像有朝霞就有落日。但是不要悲观,不要消极呀,你看看这明丽的春光吧,一切还都会生机勃勃的哟。所以去活成自己吧,去胸怀世界,探寻知识与意义吧,你还有如此美好的时光!”
愿每个人都能从泥沼中走出,躲过那凄凄的春雨,尝尝清明团子,听听后朋克,在朴素而残酷的生活中,找到自己的春天。
指导老师:胡雪健
编辑 王树坤
审读 徐卉
责编 郑力
监制 刘旭道